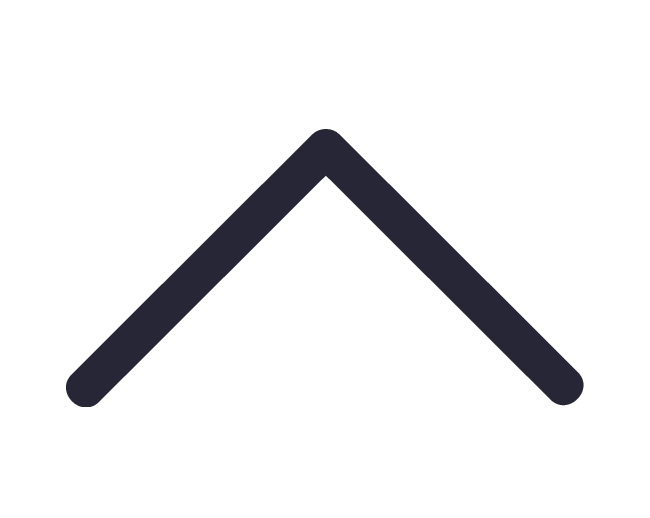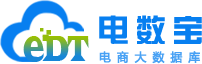(网经社讯)2020年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同一天近乎同时地公布了【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11月4日立案)、【对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11月4日立案)、【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6月23日立案),对涉案的阿里巴巴、腾讯实际控制的阅文集团、顺丰实际控制的丰巢网络违反《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的行为,依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分别做出了50万元处罚。
《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这三份处罚决定公布后,不熟悉《反垄断法》的公众更多关注的是两点:
1、50万元罚款对上一财年净利润高达1492.63亿元的阿里巴巴、933.10亿元的腾讯和57.97亿元的顺丰而言,是不是太轻了?
2、反垄断执法对中国互联网行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对熟悉我国反垄断法规则和实务的人群来说,上述两个问题并非这三个案件的看点。因为:
1、罚款上限客观地写在了法条里;
2、三个案件本身虽然涉及阿里巴巴和腾讯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并购案,但被收购的标的并非直接参与互联网市场的经营者,所以相关处罚决定严格地说还是传统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并非互联网行业的的反垄断执法。
对于熟悉我国反垄断法规则和实务的人群来说,真正关心的是:
1、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绝大多数企业是VIE架构的(极少数不是例如蚂蚁科技、苏宁易购以及拆除VIE架构回国上市的奇虎360等),且这些VIE架构企业的几乎所有并购案,在《反垄断法》2008年8月1日生效后,都没有依据《反垄断法》进行过事前的经营者集中申报(相关背景回顾参见笔者公号文章:《走出VIE架构困局的反垄断执法》);
2、2020年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这三个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都涉及的是VIE架构企业,且均是在2020年11月10日该局正式公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之前就已立案,在该指南正式颁布前查结的,而这就意味着不仅将来VIE架构企业的并购案要受到现行《反垄断法》的约束,依法依规进行申报,以往过去12年多VIE架构企业未依法申报的并购案也必须依法依规进行补报,而且还要依法依规交纳罚款,甚至不排除都是按照《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顶格处罚50万元。
笔者和部分熟悉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的学友更关注的问题则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个案层面和制度层面两个层面。
在个案层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上述三个案件的调查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
笔者最初在2017年2月27日就在向原商务部反垄断局提交【对阿里巴巴、京东等涉VIE架构互联网企业并购案涉嫌未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的举报函】时指出阿里巴巴和银泰2014年新设合营企业菜鸟网络,2017年阿里巴巴参与银泰私有化与其他VIE架构企业的并购案一样涉嫌构成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2018年8月3日再次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提交【举报:阿里巴巴未依法申报就收购银泰】。
但是,2020年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仅对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作出了处罚,并无条件批准该项并购,却没有追查阿里巴巴与银泰设立合营企业菜鸟网络涉嫌先违反《反垄断法》的问题。
那么,如果无条件批准了阿里巴巴收购银泰,阿里巴巴与银泰等企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未依法申报就组建菜鸟网络的行为是否就不查处了?菜鸟网络的组建对相关市场的到底是否存在限制竞争的影响?如果不查处这一在先的违法行为,仅处罚之后的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还是在默许这种规避《反垄断法》的行为浑水摸鱼,默许瞒天过海式的反垄断执法掩盖阿里巴巴与银泰2014年未依法申报就建立合营企业的违法事实?
具体到阿里巴巴收购银泰对哪些相关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的问题,【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仅用了“百搭”的行文一笔带过:
本机关就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一个倍受关注的反垄断案件,如此敷衍了事地论证,毫无透明度可言,等于拒绝接受外界对其执法尺度中立性、科学性和统一性的监督。
【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
2019年12月26日,笔者在【举报:腾讯视频和百度爱奇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协同操纵超前点播服务费 】谈及:
(腾讯视频和百度爱奇艺)双方作为《庆余年》第一季的共同分销渠道,必然会与该剧版权方存在交流,而该剧的出品方又恰恰包括腾讯视频,腾讯集团未依据《反垄断法》申报经营者集中就通过腾讯文学收购盛大文学成立的阅文集团,以及后者同样未依法申报就收购的新丽传媒旗下的新丽电视。
但是,与上述【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案】没有触及阿里巴巴的核心利益菜鸟网络一样,【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也根本没有涉及腾讯文学与盛大文学合并同样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未依法申报就实施经营者集中的违法事实。究竟腾讯文学与盛大文学合会被另案处理,还是不了了之?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讳莫如深。为什么?!目前,还没有媒体追问。
至于对腾讯实际控制的【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又会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哪些影响呢?相信在腾讯视频网站上有收看过腾讯视频、阅文集团联合新丽制作的影视剧的网友,也许会多少有些感触。
但是,遗憾的是,【对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只重复了【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用过的“百搭”行文:
本机关就阅文收购新丽传媒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当然,如此“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是不让外界监督的反垄断执法,显然并非这两个案件,而是从2014年12月2日起对外公开的所有50个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都是如此!(相关案件列表及处罚决定链接汇总参见笔者知乎专栏文章【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公告、处罚决定统计】https://zhuanlan.zhihu.com/p/51033675 。)
【顺丰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案】
2020年4月底5月初,丰巢快递柜调高费率遭遇一些小区业主委员会抵制的情况受到了全社会广泛关注。
例如王晓然、何倩:《涨价+并购 丰巢快递柜垄断局》,2020年5月5日《北京商报》提及
在丰巢收费风波后,头部快递柜企业进一步整合资源。5月5日,顺丰控股发布《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丰巢拟与中邮智递(中邮速递易运营主体)进行股权重组,交易完成后,中邮智递原股东中邮资本、三泰控股将合计持有丰巢28.68%股权,中邮智递成为丰巢全资子公司。
……
而获得四轮融资共55亿元的丰巢,则在2017-2019年以约40%的增速在全国铺设智能柜。据国家邮政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已经建成的智能快件箱有40.6万组,通过智能快件箱投递的快件占快件总数的10%。而按照丰巢于2019年给出的数据,其在全国已经拥有超15万个智能柜网点。意味着丰巢占据37%以上的市场份额。
袁野、吴丹若:《丰巢与速递易正式合体,4月底刚宣布超时收费》,2020年5月6日载《红星新闻》提及:
天风证券认为:丰巢收购速递易,快递柜进入寡头时代。丰巢与中邮速递易分别为当前市占率最高的快递柜运营商,截至2020年3月31日,丰巢目前投入约178000个快递柜,柜机占比约44%;中邮速递易占比约25%。收购后丰巢市占率将达69%。从网络效应来看,丰巢在一二线城市市占率更高,一线城市市占率超过70%,中邮速递易在低线城市网络更强,因此本次丰巢完成收购之后,丰巢网络效应有望进一步增强,将实现高中低线城市的全面覆盖。
2020年5月15日写邮件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建议调查:丰巢收购速递易是否涉嫌未依法申报就实施经营者集中】。此前,也有其他律师举报该项并购案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相关报道如《丰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反垄断法>?律师实名发函国家反垄断局举报》2020年05月14日载《潇湘晨报》)。
那么,这样一个横向合并实施后即导致涨价的并购案,最后为什么还是会在经过5个多月反垄断审查后,被无条件批准实施呢?
【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
仍旧近乎傲慢而又苍白地重复了“百搭”的格式化论证:
本机关就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面对这样一种武断得让外界根本“难以置喙”的反垄断法分析,曾经因为丰巢快递柜涨价而群情激愤的小区业主委员会难道会心服口服外加佩服吗?难道不会考虑依法起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无条件批准该项经营者集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吗?
在制度层面,一系列有关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制度设计问题和理论问题也仍亟需解决。
首先,如上所述,反垄断执法透明度低,首先低在大量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反垄断分析长期不公开不透明,让反垄断执法机构个案经办人员和分管领导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始终不受外界监督。
据笔者统计【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公告、处罚决定统计(2020年12月21日更新)】,从2008年8月1日至2020年12月13日,我国依据《反垄断法》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共计——3357件,算上缺乏论证但也被无条件批准的50个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合计3407个案件。这些案件的反垄断法分析都没有对外公开过。外界无法了解这些案件是否存在应禁止或者应该附加限制性条件,但没有禁止,也没有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情况。
相比之下, 从2008年8月1日至2020年12月13日,被反垄断执法机构披露的2件被禁止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被附条件批准的48个经营者集中案件,虽然有公布反垄断法分析的一些细节,但所能覆盖的行业很有限,涉及半导体和医药领域的案件居多,而且全部都是涉外案件。外界无法确信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过去12年里对内资企业主导的并购是否适用了和涉外并购案一样的执法尺度。即便是这些被公开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中,早期的近一半案件论证单薄,例如没有界定相关市场,也没有计算市场份额,同时没有说明不这样做的理由,就武断地作出了审查决定。后期的一些案件,虽然论证更翔实了,但是从来不援引原商务部反垄断局2011年9月颁布的《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导致外界不知我国执法者到底是否有受该规定约束。
可见,执法透明度低,自由裁量权大,且长期缺乏外部有效监督,并非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才存在的问题,而是贯穿原商务部反垄断局执法的老问题,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至今都没有能解决的老问题,并且在【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雷同论证里集中凸显出来,所以可能显得更具讽刺意味罢了。
其次,2020年12月14日披露的三个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里,有两个是“陈年老案”,凸显了执法者在对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件的立案上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同样不受外部有效监督。
例如,【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笔者2017年2月底举报,但2020年11月4日才正式立案。这3年多里,原商务部反垄断局及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均知道该案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为何迟迟不立案?如果立案后,只需要像今年查处时那样,仅需40天就查结放行,为何要拖3年多?
众所周知,有多位反垄断执法机构离职官员任职阿里巴巴。例如:
2014年马云通过浙江融信收购恒生电子被原商务部反垄断局无条件批准后不久,就从原商务部反垄断局离职,先后担任腾讯政府事务部研究中心总监,摩拜单车研究院院长、政府关系副总裁,美团研究院院长,现任阿里研究院资深专家、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崔书锋博士(如2019年报道《阿里研究院专家:数字经济在中外文化产业协作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6年从商务部反垄断局离职的,现阿里巴巴法律研究中心杨建辉主任(最近一次公开演讲参见2020年11月深圳大学《“经济法30人论坛”暨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理论研讨会》)。
在这种情况下,立案的拖延与不透明自然难免引发外界的丰富联想。
2020年10月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但是,对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件在接到举报或者执法者依职权发现案源线索后的立案期限没有做明确规定。笔者在2020年10月底(11月2日最后一次修订)的文章【不应回避的反垄断执法真相——驳北京大学邓峰教授所谓“反垄断合并审查的中国特色”】指出:
《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根本就没有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需要在什么期限内立案作出具体规定以至于反垄断执法人员可以把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件的正式立案无限期地拖下去,直到竞争环境貌似更有利于执法者批准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或者直到公众淡忘这些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一如笔者举报过的那些案件那样:
……
试问,既然《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可以对立案后的未依法申报案件的调查设定一个法定的期限,为什么不对自己依职权发现,或者第三方举报的未依法申报案件的核查与立案程序也设定一个期限呢?
如果在立法环节出现了这样的漏洞,那么外界恐怕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
第三,《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处罚过低,根源在2007年的立法工作,但是即便通过修法提高违法成本,也难以根本上遏制未依法申报就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情况,除非按照垄断协议查处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行为。
目前,公众普遍关注的是现行《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处罚上限50万元过低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网站人大网曾在2007年6月29日发表《明确法律责任 加大处罚力度——分组审议反垄断法草案发言摘登(五)》。在这份发言摘登中,王祖训委员就曾强调要加大对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处罚力度。2007年6月27日,《国际金融报》第2版发表文章《反垄断法二审的三个疑问》就曾对《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有关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罚款上限50万元提出质疑:
“‘50万元’这样一个金额是不是能达到“罚”款的目的,让人感到疑惑。业内人士表示,如果50万元这样的金额成立,那无疑是在反垄断的道路上放了一张‘垄断通行证’。”
从常识出发,如果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的违法行为带来的收益远大于50万元,那么又有多少经营者愿意遵守《反垄断法》的规定,对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进行事前申报呢?可惜的是,前述担忧并没能在当时受到立法者的重视,最终为大量互联网行业的VIE架构企业在过去12年里超脱《反垄断法》约束地未依法申报就实施并购与合营创造了极低的违法成本,导致了不少市场细分出现了难以补救的竞争扭曲和消费者损失。
虽然,《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第五十五条把现行《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的处罚上限调高到上年度销售额10%以下,但是没有设定处罚下限,所以还是会给执法者带来缺乏外部有效监督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容易扩大经办人员和分管领导的道德风险以及职权行使时被外力干预的可能性。而且如果违法收益足够大,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足够长,即便处罚违法者上年度销售额10%也不足以遏制其未依法申报就实施并购的冲动。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反垄断法》修订将罚款计算改为按天来计算的情况,避免违法者不配合执法,拖延事后反垄断审查进度的情况。但这些恐怕都还远水解不了近渴。
笔者认为,未依法申报并获得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本身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效力待定行为。所以,在拿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正式批准之前,参与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经营者应当还是被视为《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彼此独立的经营者,他们之间任何横向的整合,或者纵向的合作,都属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横向垄断协议或者纵向垄断协议。这样,即便不修改《反垄断法》,仍旧可以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按照垄断协议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同时还可以保障受到这类违法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向违法者索赔。唯有如此才能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形成足够的法律威慑。
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家之言,而且早在2011年《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时就曾经向原商务部反垄断局谏言,但没有被该局采纳。
最后,笔者想在此对部分学者有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0年12月14日处罚的三个未依法申报案件的解读提出一些批评。
早在2014年,笔者就曾经在澎湃新闻发表文章《盘点反垄断案例③|三大执法机构选择性办案?》指出:
……本应真正信仰市场竞争、最该具有竞争文化的反垄断法学者们,却显得始终都“一团和气”。和欧美反垄断法实践往往招致旷日持久的公开辩论,以至于学派林立、理论创新层出不穷的繁荣景象不同,每每有媒体披露反垄断执法、诉讼中的大案要案,都会有至少一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以及若干知名反垄断法学者,在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为相关执法、司法实践背书、点赞。
2020年了,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对阿里巴巴、腾讯阅文集团、顺丰丰巢的处罚决定后,又涌现了一些学者对前述存在不少问题的反垄断执法实践给与“缺乏法治营养”的点赞、背书,甚至刻意和【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保持一致,或掩饰,或回避原商务部反垄断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在过去12年多里对互联网行业大量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不予以追查——这一众所周知的“秘密”。例如:
王先林:《解读三起未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罚案》,2020年12月15日 载中国经济网
张晨颖:《对协议控制(VIE)下互联网平台企业未经申报违法实施集中处罚的案例分析》,2020年12月21日 载《经济日报》(全文链接如http://news.ifeng.com/c/82O6rpiqG0T )
钟鸿钧:《总局反垄断罚款50万!专家:体现了非常专业的监管水准》, 2020年12月19日载市场监管半月沙龙
上述三位学者对2012年8月13日【商务部公告2012年第49号 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沃尔玛公司收购纽海控股33.6%股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都避而不谈。难道他们都不知道该案也是涉及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吗?还是他们被要求不准提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是熟悉中国反垄断法理论与实务的人都了解的,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会议上都曾经被讨论过。有什么好回避的呢?
笔者2012年8月就曾在新浪微博和博客对商务部反垄断局对沃尔玛收购钮海1号店附加与VIE架构有关的限制性条件深表忧虑(如《为什么要在锐邦诉强生和沃尔玛购纽海案上较真?_绍耕_新浪博客》),2016年6月23日再次在《京东联姻沃尔玛背后的反垄断审查》中对该案进行反思。
在互联网业界,早在2013年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就曾公开指出《科技大佬上两会:马化腾重信息安全 李彦宏挺VIE》:
“以国内投资并购领域为例,企业投资并购对象为年营业额4亿元人民币以上企业时,需按规定向商务部申请经营者集中审查,一旦涉及VIE问题均无法被正常受理。”李彦宏在提案中提到。
同样,阿里巴巴也曾在2017年11月27日的一份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中提及原商务部反垄断局不接受涉及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材料,导致相关反垄断审查无法进行,阿里巴巴的相关并购面临不确定性和法律风险。
【Filed Pursuant to Rule 424(b)(5) Registration Statement No. 333-221742】
In addition, MOFCOM has not accepted antitrustfilings for any transaction involving parties that adopt a variable interestentity structure. Our ability to carry out our investment and acquisitionstrategy may be materially and adversely affected by MOFCOM's current practice, which creates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as to whether transactions that we may undertake would subject us to fines or other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ndnegative publicity and whether we will be able to complete large acquisitionsin the future in a timely manner or at all.”
不承认我国商务部反垄断局早在2012年就审查过涉及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就可以掩盖2020年12月14日以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长期对互联网行业并购案不作为的事实吗?对于由此带来的问题,即便不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相关负责人追责,学者连提都不能提,提都不敢提了吗?
另外,钟鸿钧认为【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顺丰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案】、【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的处罚决定“体现了非常专业的监管水准”。这种评价,相信很多人都和笔者一样难以认同。
首先,【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顺丰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案】、【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的处罚决定有关相关并购对竞争的影响分析都只有同样的一句话
"本机关就……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试问,从这样一句空洞无物,高度抽象到完全不透明的“评估”中,作为一位经济学教授,钟鸿钧是如何看出“体现了非常专业的监管水准”的?
当然,不排除钟老师参与了上述三个案件的论证,所以了解更多没有被公开的细节。但至少从目前上述三个案件公开的处罚决定表述来看,外界恐怕很难断言这三个案件的处罚决定本身“体现了非常专业的监管水准”。
另外,从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作出反应的响应度和调查周期来看,【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顺丰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案】、【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三个案件完全不是一个监管水准。
【顺丰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案】是在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实施后2个月内就立案的,但前前后后查了5个多月。
【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发生在2017年,当年被举报,违法行为持续了40个月左右,2020年11月4日才立案,然后用40天查结!
【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发生在2018年,就算是2019年被举报,违法行为持续了27个月左右,竟然也在2020年11月4日,和【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同一天被立案,而且和【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一样用了40天查结。怎么就都这么巧合的?!
结果,三个案件,【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是【顺丰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案】的大约20倍,是【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大约2倍,但最后三个案件的罚款都是50万?仅仅因为【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在答记者问】给出的如下理由吗?
上述几家企业在行业内影响力较大,投资并购交易较多,拥有专业的法律团队,应当熟悉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但未能主动申报,影响较为恶劣,因此决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予以顶格处罚,希望达到查处一批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目的。
那么,在商务部行政处罚决定书(商法函[2018]130号)中处罚的【青岛港招商局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与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未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的起始日期为2009年12月18日,立案日期为2017年8月9日,前后历时8年多,可最终两家违法企业仅仅依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各处罚了20万元人民币,加起来还没有前述2020年12月14日查处的一个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多。
那么,为什么当时对【青岛港招商局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与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案,没有因为“几家企业在行业内影响力较大,投资并购交易较多,拥有专业的法律团队,应当熟悉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但未能主动申报,影响较为恶劣,因此决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予以顶格处罚,希望达到查处一批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目的”?
张晨颖老师在《对协议控制(VIE)下互联网平台企业未经申报违法实施集中处罚的案例分析》中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往对未依法作出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处罚金额进行了统计,为什么没有能公开质疑反垄断执法者在罚款金额设定上自由裁量权过大,长期处罚额度过低的问题呢?为什么没能追问,2014年12月2日紫光收购锐迪科因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被公开处罚前【商务部行政处罚决定书(商法函[2014]788号),为什么原商务部反垄断局都没有披露过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处罚决定,且至今对2008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1日前的这类处罚决定都没有公开过呢?
难道,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设立不应当为依法治国服务吗?难道该专家咨询组的成员不应当对反垄断执法工作予以监督,包括作出公开批评和追问吗?
如果熟悉反垄断法的专家、学者都不去公开地监督反垄断执法工作,那么谁还能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资历、学术权威和话语权,来监督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敦促起纠正工作中的不足呢?
为什么,从2008年8月1日到2020年12月14日以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执法都裹足不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学者及相关领域的经济学者,是否都有责任呢?
除了很早以前就在新浪微博(ID:竞争法研究)上呼吁互联网行业开展反垄断执法,
2015年10月15日,笔者曾在澎湃新闻发表《规范专车,小心走音》时指出: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领域至今尚无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被申报的案例,更没有未依法申报而被罚的案例。
2016年8月至今笔者在十几篇文章中呼吁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对滴滴收购优步中国案展开调查,公布调查进展(相关文章汇编《网约车行业反垄断调查呼声又起,以往学者对滴滴收购优步中国案观点再梳理(+投票) 》)
2016年9月13日,笔者在澎湃新闻发表《金融业反垄断执法难,从支付宝提现收费谈起》逐条批驳了主张“《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互联网业”的三种代表性理由。
2016年12月9日,笔者发表《梁建章又“隐退了”,但携程去哪儿“联姻”涉垄断的迷雾没散》,呼吁对在线旅游平台的并购案开展反垄断调查;
2017年3月24日,笔者在澎湃新闻发表《阿里收购大麦网,但说好的反垄断审查呢》,再次呼吁执法者重视互联网行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2018年08月29日,再次在澎湃新闻疾呼《反垄断执法不应纵容互联网寡头》
……
在回顾自己【发表在媒体上的反垄断法时评110篇及专访】时,笔者也很感叹,更慨叹,有关呼吁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的文章占了快近乎一半。但,一个人的呼声是有限,最终还是需要有更多人,能够支持互联网行业强化反垄断执法,支持所有行业都可以支持反垄断执法,都可以重视反垄断法合规。那么,总有一天,我国将不再需要“强化反垄断”这样的提法,因为在社会的有效监督下,高效透明、持续推进的反垄断执法已经让反垄断法合规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一部分了。
笔者相信会有这样一天。
而这样的努力,可以从2020年12月14日全民关注的这三个反垄断执法处罚决定开始,因为它们本身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在短短的一两周内唤醒了全民对反垄断法落实的希望和支持反垄断法落实的热情。